新观察系列#总1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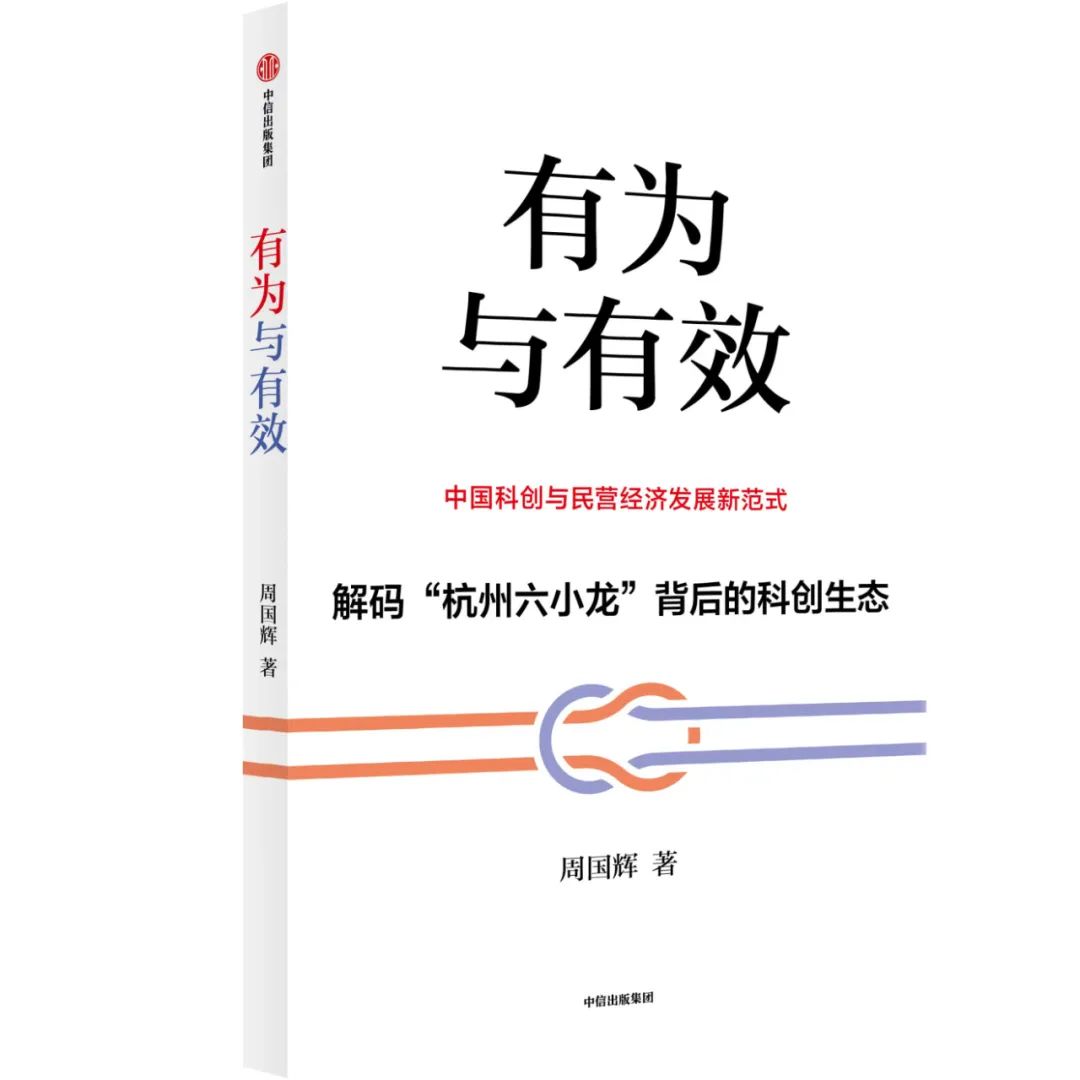
2025年5月10日成稿
▼
日前在浙商杂志网上,读到记者对《有为与有效 ——中国科创和民营经济发展新范式》一书作者周国辉先生的访谈。全文篇幅虽然不长,但非常全面而精准地表达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内容精髓,完全可以视为本书的一篇追加“前言”,读来很受教育,也很受启发。
再细看“解码‘杭州六小龙’背后的科创生态”副标题,便可大体得知:此书拟从剖析“杭州六小龙”现象入手,阐明作者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层思考。所谓的“有为”,即为“有为政府”;所谓的“有效”,即为“有效市场”。在作者看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密不可分、良性互动,是“杭州六小龙”破圈走红的奥秘所在,也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理想境界。

的确如此,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决策以来,我国就在同步推进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最初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1981,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1987 ,党的十三大) ,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 ,党的十四大)——体制模式的概括和相应“名头”的一再调整,表明了我们党和国家对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目标的认知深化和逐步明晰。即便党的重大文献一再重申最近30多年来稳定不变的结论,顶多增加了一些“高水平”之类的递进修饰语,但那也无法表明人们的观念,已然达致了“实践出真知”的水准。对此,无论是从理论的系统构建,还是从实践的坚定执行,我们今后要走的路都还很长,距离要达成的理想境界都还很远。
其实,作为当下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并非原先所谓的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人们对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更多的还是自觉不自觉地从平面化的角度去看待的。譬如两者谁也离不开谁,或是谁更多一点还是谁更少一点,如此等等。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更应当从立体化的角度去把握,它实质是一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这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成为和当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一种生产关系时,其总和就构成为我们现实的经济基础。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基础第一性“决定”,和上层建筑第二性“被决定”的关系。尽管在特定条件下,“被决定”者的“反作用”,有时看来还会对“决定”者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但这也改变不了从总体上、从根本上而言的两者之间关系。如果硬要坚持将特例视为常态,并执意要在实际生活中归于正常,那就会迎来马克思在上文中所说的“社会革命”。或者换句他讲过的更为透底的话来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譬如市场经济,笔者注),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很多人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句话不甚了了;也不清楚为什么十年之后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还要一再重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因为,很多人光知道背诵某些现成的结论,但并没有往深里想明白:所谓“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更好”,应该也只能是体现在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确实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上,而不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本末倒置,反而是让政府及其官员“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不是说党和国家领导经济工作有什么不对。但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对”,是建立在领导者对经济运行现状和问题的实事求是之中的,是基于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谦卑敬畏之上的,也是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认知和行动的必然结果。脱离这些个前提条件,政府作用的发挥能否算是“更好”,恐怕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出现反而“更坏”的结果。
政府对于自身在经济生活中能起到的作用,还是要懂得感恩和回馈。没有市场主体提供的税收,政府和官员就无从做事,更无由生存。阳光雨露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生态所固有的,并非由政府凭空“提供”出来。政府若能提供“阳光雨露”,让市场主体“茁壮成长”;那就意味着政府也能提供“暴风骤雨”,让市场主体“不得好死”。无论是出于善意的恩赐,还是流于恶意的打压,恐怕都是一种市场和政府关系认知上的错位。不但政府不应当这样去做,更不能由此成为一些官员对市场及其主体趾高气扬、颐指气使的“气眼所在”。
那“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又何以体现呢?除了上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外,那就是遵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要求,信守“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准则,协调运用人文、政治、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包括必要的制度供给和行政执行,营造一个“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维护一个进取向善、“国泰民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曾忧心忡忡于实行“四万亿”的刺激政策,或会带来某种旧观念的“沉渣泛起”和旧体制的“卷土重来”。从后来的经济工作实践来看,这种担忧也不无道理。笼统地指责“国进民退”或许不一定合理,但在竞争性领域中如果出现大面积的“国进民退”,那不过是思想理论上“政(政府)进市(市场)退”的一种必然表现。这也恰好证明,中央一再重申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有关论述,绝非空穴来风、无病呻吟。
“杭州六小龙现象”的厚积薄发,实证了多年来杭州“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的政府作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我们也不要因此把话说得太满。本书作者周国辉先生当年率先提出浙江科创人才“新四军”一说,我以为其中最具远见卓识的,还是明白无误地将“阿里系(科技+民营)”纳入其中。假如杭州有的人觉得发展“互联网+”新经济(现为“人工智能+”,均为数智经济)并非所谓的实体经济,因而再去简单笼统地强调发展制造业,同时又未能及时将“六小龙现象”聚焦引导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上,那杭州未来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又会走向何方呢?
背景文章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