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杂谈系列#总1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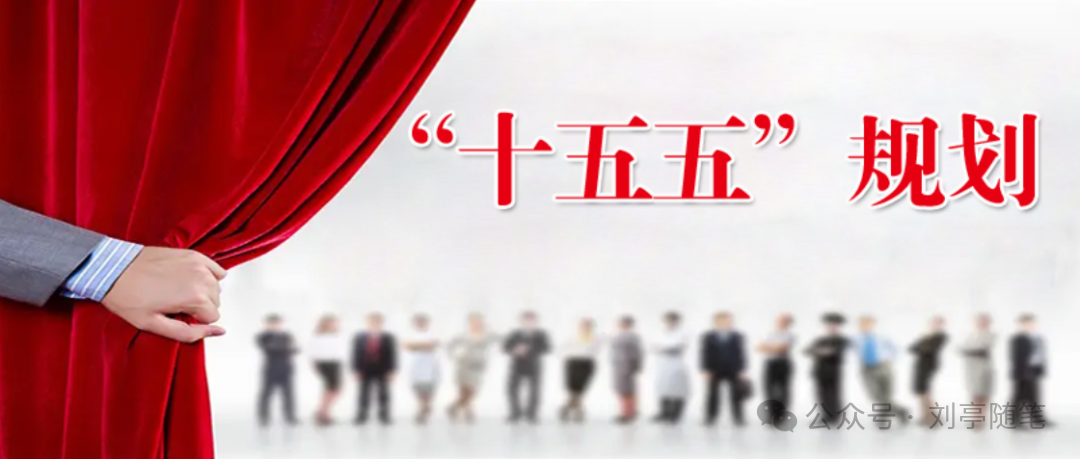
“去年的4月和7月间,曾以《“十五五”杂谈》为系列,在我实名公众号上发过五篇随笔。眼见得已进入“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的“冲刺”阶段,遂再捡起这一话头,接着划拉几篇东西。日前饶有兴趣地拜读了徐林先生的一篇3万多字长文,感触良多。作为深读的一个环节,于是想着多少说上几句,这是之三……”
2025年7月1日成稿
▼
《比较》杂志编辑室和徐林先生的对谈话题,转到了“十五五”预期的GDP增长率上来。毕竟这是中长期规划指标体系中,最基础、最综合、最核心的指标了。他在对确定指标的方法作了一番回顾和分析以后,最后给出的正面结论是:“‘十五五’ 期间不适合提出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如果能在有效增长基础上尽可能扩大就业效应,并有效控制总体债务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能实现4%左右的年均增长就很好了。”
我在之前对此的想法是5%左右,并强调“事实上,没有一定的、好比说5%左右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宏观形势难以保持必要的稳定。虽然转型发展期不应过多地在意和纠缠经济增速的高低,但那是在增速不至于动摇起码的预期和信心的前提下。”
我在这段话里的潜台词是:“十五五”“起码的预期和信心”之底线,是GDP增长5%。以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还在相当大程度停留在粗放增长和外延扩张的水平上,我们的统计数据又包含了诸多水分,特别是事实上的KPI指挥棒齐刷刷地指向GDP的情况下,能保持规划期内5%的年均增长率,已属于上上大吉。
徐林分析指出的4%左右的增长率,是客观中正、也是求真务实的。如果全社会的认知,都能彻底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4%货真价实的增长,本是件很好的事情。但以我多年参与编制省域中长期规划纲要的体验,这或许会被认为是偏于悲观和保守,不利于提振士气、鼓舞人心。

我在近年来一反常态地强调经济增速的原因,本意是针对那种日益见长的对于经济工作的边缘化甚至是漠视的现象。仿佛这世上的事情,就是大把花钱、只管借钱却无须赚钱。哪有什么“但事耕耘、莫问收成”的好事?!百业凋零、坐吃山空,那民生和就业都是难以为继的。
对于之前国家宏观政策重点取向往需求侧一方的调整,我觉得确有必要。但那也仅限于短期应急,反周期调节的需要,目的是为了“让向前骑行的自行车不至于倒下”。但经济刺激政策必须要有底线,要有节制。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总也走不出“印钱创造需求、债务驱动投资”的路径,前途委实堪忧。巨额债务势必反噬发展,最终难逃“增长陷阱”。因此,“十五五”一大要务,是要尽力摆脱这种“路径依赖”,投资增长包括整个经济增幅,或许都需要相对保守一些。
说到底,结构性改革还是要解决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这方面徐林的分析尤其到位,值得反复研读,深入理解。当《比较》杂志相当尖锐地问及“‘十五五’期间中国是否还应该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从‘十三五’规划就提出的主线”时,徐林马上回应道:“你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涉及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究竟是什么,未来的政策和改革重点究竟在供给侧还是需求侧?这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的增长模式、增长效率和增长可持续性。”
之后他摆明了结论:“从增长的角度看,重点应该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足够有吸引力和正向激励的制度和发展环境,鼓励各类市场主体更高效地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形成具有竞争力和市场效益的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转型升级,形成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持续动力。”在他看来,虽然对此中央早有提出和重申,但在实践中的进展并不理想:一来为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目标所累,不得不借重扩大债务规模以刺激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二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和影响越来越大,与“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要求,则渐行渐远。
当然,徐林这样说,也不意味着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重要性的忽略。当编辑室追问对“十五五”扩大内需政策的态度时,他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在他看来,周期性减速因素的对冲、疫情“疤痕效应”的消除,居民资产缩水及预期转弱的拉抬,都需要刺激性政策的缓解和弥补。只不过扩大需求,我理解应以扩大内需优先;扩大内需,应以扩大消费需求优先;扩大消费需求,又应以扩大服务消费需求优先。而且,政府花钱一定要和“买制度”相结合,譬如着眼于削减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所谓“四座大山”,而对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的拾遗补缺、“填平补齐”。

记得当年自己所参与的省域“十二五”规划《纲要》,曾极为突出转型发展的重要和紧迫。不但在开头部分强调“加快推进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以创新促转型,以转型促发展,努力开创具有浙江特点的科学发展新局面。”最后还不忘首尾呼应,再重申一遍:“‘十二五’规划是坚持科学发展、推进转型发展的重要规划”。
但在整体发展态势尚且一马平川、顺风顺水之时,那种对于转型发展的鼓呼,其实没有什么针对性,也很难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百年未有之大变之下的高度不确定性,传统发展模式明摆着的不可持续性,这些年来因为转型发展迟滞所带来的被动性,已将未来五年的发展重点昭然若揭。
不是说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提出得晚了,包括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以及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地位的要求,提得都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但是实际工作的推进,却算不上得力和到位。高科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包括军工科研和生产,亮点多多,但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而言,就企业、个人和社会认知及行为的自觉而言,传统发展模式运行的惯性还未能有效改变,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进展乏善可陈,“十五五”已然到了一个非有大转型而不足以有效应对困境、赢取战略主动的关口。
那么,具体的转型主要包括什么内容呢?徐林清晰而精准地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的共四条对策:“经济方面的结构转型主要是服务经济转型、数字智能转型和绿色低碳转型,另一个是经济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他强调:“这四大转型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所在。”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