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自“大包干”的农村改革肇始。而这一带有颠覆性意义的变动,之所以能得以破题和成功,又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理论命题相关的拨乱反正紧密相连的。正因为是想到了这一层,我才将本文题目最终确定为:“正本清源话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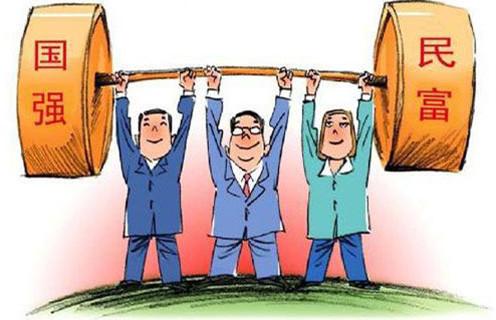
去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命题,对此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看见吴敬琏老先生的这篇讲座稿,以为是正本清源之说,于是才拿来好好推介一番。
小编的“标题党”做得不错,拎出了冗长记录尾部的关键一句话,将全文定题为:“结构性改革是制度改革,不是政府调结构”。我很以为然,否则这个时候推出这个命题还有什么价值?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讲,直白地点明“体制改革”也就是了,又何必曲里拐弯、生出这许多让人想象和发挥的空间!但老先生解释得好,既然我们自己也号称“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安排所差无几,那人家在此既定前提下将制度性的改革统称为“结构性改革”,咱也来“东施效颦”一下吧!
新命题推出,但从不做正面解读,甚至连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也不讲明,任由各路专家(砖家)自以为是、各抒己见。结果闹得本该“一言定尊”的理论表述,整得沸沸扬扬、乱乱哄哄。这个毛病,不止一次出现过。记得2010年将15年前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式调整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没见着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班的专题讲座中交代清楚。于是乎,我们还真能看到“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官场百态;而重大的理论创新,便沉沦为人云亦云的政治口号了。
老先生不但把“结构性改革=体制改革”的窗户纸一下子捅破了,令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关键还通过对经济下行成因的深度挖掘,对高层决策过程的系统回顾,阐明了上述公式不容置疑的确定性。经济为何下行?又如何应对?吴老先生在高度抽象后理出了两条“脉络”:一是以需求侧为重,因而摆在第一位的,是要靠凯恩斯式的“行政性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二是以供给侧为重,因而摆在第一位的,是要靠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结构性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
一开始国家倾向于前面这条“脉络”,2009年短期效果不错,全世界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但很快就开始出现“边际效用递减”、同时“债务风险倍增”的现象。如此这般,依惯性一路滑行到2015年,眼看着投资拉动效用“归零”,全社会杠杆率已高达百分之250到300的“超警戒线”,而经济增长率则一个点一个点止不住地往下滑,这下子“瞌睡醒了”:再也不能这么干了!于是痛下决心改弦更张,于是才有了现如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过程大略如此,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插曲,就是1995年中央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2010年调整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且明确作为“主线”,其内涵、定位和方向都是对的,但效果却“很不如人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未能触及实质性的改革!奶酪不动,改革“挂空”,其必然结果就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年复一年、山河依旧”。所以,推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后期,高层越来越强调要坚决破除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而新一届的党中央,则再次高举起“全深改”的大旗。
就此而言,新命题的提出,其意义主要是在于将以供给侧为重的宏观调控方针,和着眼于破解体制机制顽疾的“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从而进一步明确了通过市场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以此拯救和发展中国经济的“主线”。对此,最新发布的权威人士言论作如是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往远处看,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见《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
把这一命题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联系起来,便已非同小可了。如果再将跨越陷阱和实现中国梦相连,那就更加是“宏大叙事”了。吴老先生的解读,能和权威人士产生如此契合的“良性互动”,想想“也是醉了”。
也有人说,那些个理论命题都是“虚的”,玩不玩没多大意思。我觉得这可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不说毛泽东曾经讲过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想当年列宁也曾有这样的断语:“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执政党如果没有把自己领导的国家如何科学发展的理论搞明白,实际上也是“难当大任”的。至于个别人不动脑筋,或顾名思义、或望文生义,对严谨的理论命题做任意曲解,又或是高高挂起、不接地气,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这一点儿也不能成为贬低或漠视科学理论的正当理由。
全球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自“大包干”的农村改革肇始。而这一带有颠覆性意义的变动,之所以能得以破题和成功,又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理论命题相关的拨乱反正紧密相连的。正因为是想到了这一层,我才将本文题目最终确定为:“正本清源话改革”。
(本文成稿于
背景文章: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